乌克兰和加沙:结束敌意需要秩序,而不是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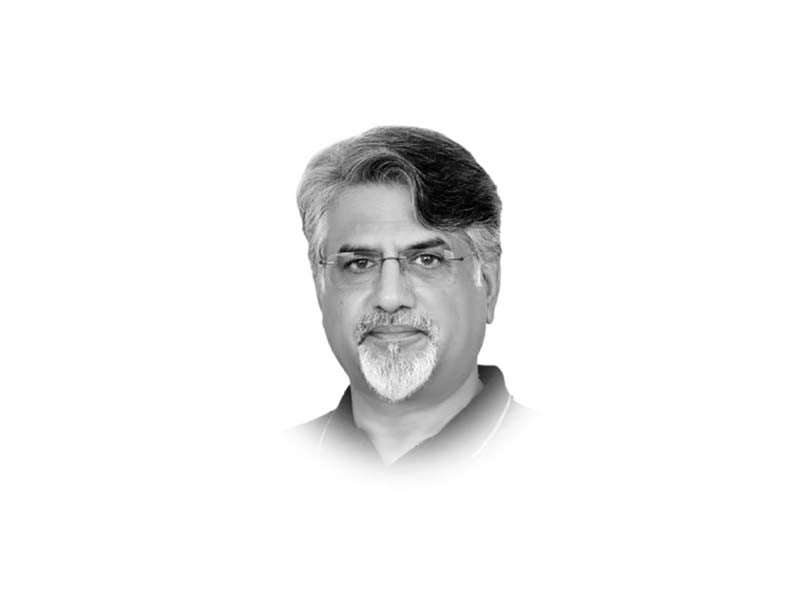
历史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而且也是关于变化的。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的变化,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从历史教给我们的教训中受益。条件、环境和环境都在变化,当我们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时,我们意识到,过去的一些类比是非常相关的,但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它们可能被复制的变化的环境时,我们才能从中受益。对于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那些属于现实主义思想学派的学者来说,和平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或可取的目标。只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才能实现和平,而促进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力量平衡。由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的,我们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和平,而是一个或多或少和平的环境和条件。解决一场中东冲突和另一场乌克兰冲突是目前全球和平议程的首要任务。
本文旨在借鉴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引用类比,看看为什么这些冲突无法解决。首先,我想引用亨利·基辛格的话,他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创造秩序,而不是和平。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他创建了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中东秩序。他通过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中东追求秩序,而不是和平。
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伍德罗·威尔逊属于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作为美国总统,他追求着著名的“威尔逊式和平”,这给基辛格等外交家的理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威尔逊式的和平只导致了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和他后来对欧洲的征服。这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结束了自由主义追求和平的议程,并使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相信,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永久和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Emauel Kant)早些时候曾写道,战争状态最终会导致任何交战国家精疲力竭,他们更喜欢和平而不是战争的痛苦。我相信,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都饱受战争的折磨,外交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努力在这两个地区创造秩序,而不是和平。
但首先我想让读者了解这些地区环境的变化,为此我将这些地区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90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在中东,美国无意推动民主;独裁是维系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粘合剂。然而,当哈马斯在加沙和西岸赢得自由公正的选举时,它被拉到一边,不被承认。就连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民主政府也在2013年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
当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地位正在减弱,但它继续追求两个目标:一是继续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并将北约(NATO)向东扩张;二是与伊朗共享中东地区,防止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出现。
第三个时期,从2010年到2020年,特朗普总统推翻了奥巴马总统与伊朗分享该地区的政策,转而对伊朗发起“最大压力运动”。“阿拉伯之春”始于2011年,美国无法再保证其支持的一些阿拉伯政权的生存。在这一时期初期,俄罗斯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它收回了克里米亚,并来到中东支持其附庸国叙利亚的失败政府。在这个时代,另外三个主导因素改变了中东政治的动态。第一,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仅在中东地区就投资了1230亿美元。其次,被剥夺了核协议权利的伊朗开始重申自己的立场,并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而美国未能对此作出回应。第三,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成为首位改变了地区和世界观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无法找到军事解决也门政治危机的办法,中东持续的人道主义苦难和内战,以及美国未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促使他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
目前,乌克兰深陷困境。它让自己被寻求更大战略目标的外部势力所利用。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停滞不前,可能面临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同样的命运。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安瓦尔·萨达特的第3集团军在为期6天的萨尼亚半岛战争中几乎面临同样的命运时,外交取得了胜利,埃及第3集团军没有被摧毁。这种外交干预使萨达特得以在尊严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签订和平协议。泽伦斯基总统还必须能够在与俄罗斯谈判时保持尊严。
在乌克兰问题上,世界需要遵循同样的模式。外交必须进行干预,世界必须寻求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在该地区建立秩序。在伊朗问题上也应采用类似的方法。伊朗需要融入该地区,而不是被视为“抵抗轴心”的一部分。俄罗斯和伊朗还必须同意外交手段可能提出的在这两个地区建立秩序的公正和公平目标。
在过去30年里,美国在操纵国际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期在战略上占据上风。今天,大国不再准备屈从于美国的军事化外交政策。确保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外交是正确的前进道路。一切寻求解决目前冲突的军事化企图只会把各地区和整个地球推向不必要的不确定和不稳定。
历史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而且也是关于变化的。我们阅读历史是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但如果我们不了解历史的变化,我们可能永远不会从历史教给我们的教训中受益。条件、环境和环境都在变化,当我们把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代时,我们意识到,过去的一些类比是非常相关的,但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它们可能被复制的变化的环境时,我们才能从中受益。对于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那些属于现实主义思想学派的学者来说,和平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或可取的目标。只有为战争做好准备,才能实现和平,而促进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力量平衡。由于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的,我们永远不会有绝对的和平,而是一个或多或少和平的环境和条件。解决一场中东冲突和另一场乌克兰冲突是目前全球和平议程的首要任务。
本文旨在借鉴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引用类比,看看为什么这些冲突无法解决。首先,我想引用亨利·基辛格的话,他认为我们应该努力创造秩序,而不是和平。作为一名美国外交官,他创建了一个持续了30多年的中东秩序。他通过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实现了这一目标——在中东追求秩序,而不是和平。
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家伍德罗·威尔逊属于自由主义思想流派,作为美国总统,他追求着著名的“威尔逊式和平”,这给基辛格等外交家的理解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威尔逊式的和平只导致了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和他后来对欧洲的征服。这一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结束了自由主义追求和平的议程,并使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相信,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永久和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8世纪伟大的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Emauel Kant)早些时候曾写道,战争状态最终会导致任何交战国家精疲力竭,他们更喜欢和平而不是战争的痛苦。我相信,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都饱受战争的折磨,外交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努力在这两个地区创造秩序,而不是和平。
但首先我想让读者了解这些地区环境的变化,为此我将这些地区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90年代,苏联解体,俄罗斯失去了大国的地位。在中东,美国无意推动民主;独裁是维系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的粘合剂。然而,当哈马斯在加沙和西岸赢得自由公正的选举时,它被拉到一边,不被承认。就连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民主政府也在2013年得到美国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
当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美国作为单极大国的地位正在减弱,但它继续追求两个目标:一是继续蚕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并将北约(NATO)向东扩张;二是与伊朗共享中东地区,防止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出现。
第三个时期,从2010年到2020年,特朗普总统推翻了奥巴马总统与伊朗分享该地区的政策,转而对伊朗发起“最大压力运动”。“阿拉伯之春”始于2011年,美国无法再保证其支持的一些阿拉伯政权的生存。在这一时期初期,俄罗斯已经崛起为一个大国,它收回了克里米亚,并来到中东支持其附庸国叙利亚的失败政府。在这个时代,另外三个主导因素改变了中东政治的动态。第一,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仅在中东地区就投资了1230亿美元。其次,被剥夺了核协议权利的伊朗开始重申自己的立场,并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而美国未能对此作出回应。第三,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成为首位改变了地区和世界观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无法找到军事解决也门政治危机的办法,中东持续的人道主义苦难和内战,以及美国未能向沙特阿拉伯提供安全保障,促使他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
目前,乌克兰深陷困境。它让自己被寻求更大战略目标的外部势力所利用。乌克兰军队在库尔斯克的进攻停滞不前,可能面临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同样的命运。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安瓦尔·萨达特的第3集团军在为期6天的萨尼亚半岛战争中几乎面临同样的命运时,外交取得了胜利,埃及第3集团军没有被摧毁。这种外交干预使萨达特得以在尊严完好无损的情况下签订和平协议。泽伦斯基总统还必须能够在与俄罗斯谈判时保持尊严。
在乌克兰问题上,世界需要遵循同样的模式。外交必须进行干预,世界必须寻求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在该地区建立秩序。在伊朗问题上也应采用类似的方法。伊朗需要融入该地区,而不是被视为“抵抗轴心”的一部分。俄罗斯和伊朗还必须同意外交手段可能提出的在这两个地区建立秩序的公正和公平目标。
在过去30年里,美国在操纵国际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以期在战略上占据上风。今天,大国不再准备屈从于美国的军事化外交政策。确保在这两个地区建立以均势原则为基础的秩序的外交是正确的前进道路。一切寻求解决目前冲突的军事化企图只会把各地区和整个地球推向不必要的不确定和不稳定。